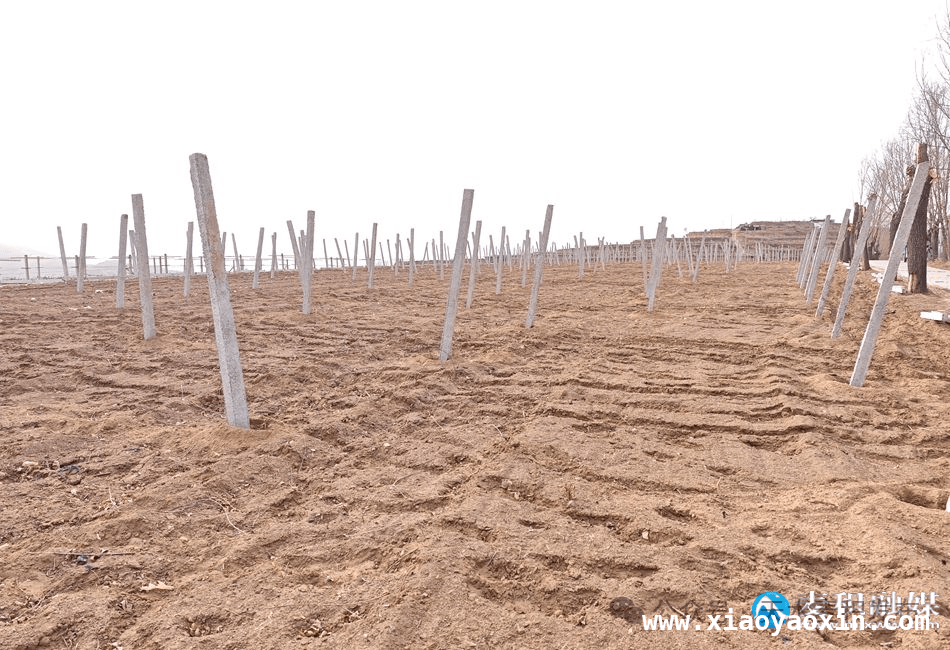本文围绕岭南醒狮展开,讲述了其面临的商业化困局、发展历程、标准化进程以及商业化尝试,还介绍了长岭等地在醒狮推广方面的举措,最后提到十五运将为醒狮带来新契机。
2005年,在某个岭南村庄里,曾经名震十里八乡的“狮王”,如今满脸颓丧地窝在一间逼仄的小店里,靠贩卖咸鱼维持生计。这便是电影《雄狮少年》中“咸鱼强”的出场画面。而现实里,醒狮也长期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
一方面,醒狮文化根系庞杂,深深扎根于民间。无论是盛大的庆典,还是热闹的节日,总能看到醒狮活跃的身影,其传承脉络从未出现断层。另一方面,“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不断上演,龙狮行业始终深陷商业化困局。
在市场化大潮的拍击下,醒狮一度陷入一种艰难的状态,仿佛不存不济。不过近年来,传统非遗重振声量,先是英歌舞一夜之间蹿红网络,龙舟赛百舸争流迅速破圈,后来机器“赛博狮”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而,作为一项产业,醒狮依旧发展得平淡无奇。
据不完全统计,偌大的广州有五百余支狮队。这些狮队作为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者,从祠堂那袅袅的烟火中一路走来。如今,它们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如何穿越城乡巨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周期,怎样与新式的、赛博的东西相融?醒狮又该如何在市场化大潮中安身立命,实现自我造血?城市又要怎样将这一文化符号锻造为独特IP,为自身的风貌和文旅发展赋能呢?
今年年底,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其中广州赛区将承办开幕式以及40%的竞赛量。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岭南醒狮将登上开幕式的舞台。在现代体育大放异彩的当下,传统非遗体育也被寄予厚望,期待能释放出更大的声量。
2015年,在广州市黄埔区,70多岁的水西醒狮老队长找到了在长岭街道工作的钟伟光,希望他能重建狮队。同时交到他手中的,还有一只狮头、一面破鼓以及仅存的两名队员。
曾经盛极一时的水西醒狮斩获过无数奖项,但最终还是难逃没落的命运,这其实也是广州众多狮队的真实写照。
广东醒狮融合了武术、舞蹈、音乐等多种元素,它起源于唐代宫廷狮子舞,随着中原移民传入岭南后,与本土浓郁的商业气息和宗祠文化相互交织,形成了以采青、祭祖为主的活动场景。多位传承人、狮队负责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醒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醒狮活动开始逐渐普及,大多数狮队都是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的。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代表性传承人、广州市龙狮协会常务副会长龚桂冬回忆道:“那时候农村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小孩子五六岁就跟着大人看、模仿。我们这一辈多多少少都有基础。”这也说明醒狮有着深厚的底子,具备良好的复兴条件。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的退缩,使得醒狮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特别是在“世界工厂”广东,醒狮无奈地跌入了巨大的城乡二元裂缝之中。越来越多狮队的主力和传承人不得不像“咸鱼强”一样,选择淡出、离开,进入新的社会分工秩序。
龚桂冬表示,在这一时期,除了猎德等部分富饶的村子仍愿意掏钱维系狮队外,其他村落的狮队大多默默消失,或者仅在家族层面保留最原始的拜祠堂功能。
2006年,广东醒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政策的关照,醒狮活动开始逐渐复兴。特别是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发布,非遗保护工作趋向“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一系列相关政策密集出炉。
也是在这一年,水西醒狮队开始重建。钟伟光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他在村里发布公告,先招募30岁上下的同龄人,再通过日常表演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加入。到如今,仅本村队员就发展到了五六十人,学生逐渐成为狮队的主力。
2007年,出于对本村青少年乏人监管的担忧,龚桂冬在黄埔区小坑村也重建了醒狮队,并一年四季保持训练。狮队重建后,临近村庄的孩子一度十分活跃,但不久后,龚桂冬发现这些孩子渐渐消失了。经过多方打听,他才意识到:“原来醒狮是有宗族性的,老一辈不愿意让本村孩子去外姓祠堂训练。”于是,他与黄埔区进行沟通,将训练场地从龚氏宗祠转移到了区文化馆,并成立了“弘毅国术会”。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村村有狮队也意味着,醒狮的推广还需要克服“十里不同俗”的问题。醒狮的标准化历程与广州也有着颇深的渊源。1985年元旦,全国第一个醒狮社团——广州工人醒狮协会在广州成立。而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直到十年后才出现,并开始编制统一的赛事规则,从业者也逐渐有了教练员、裁判员等专业资格认证。
在弘毅国术会不远处,青砖白柱的龚氏宗祠门口,醒狮训练用的高桩依旧静静地矗立着。
从近50年来岭南醒狮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既依靠宗族汲取生息,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受到宗族的限制,最终还是要走向普适化、标准化。龚桂冬大致核算过,“巅峰时期,广州每条村落,甚至学校、工厂都有自己的狮队。”到如今,全市仍存留有五百多支狮队。

据悉,弘毅国术会采取“合作制”的模式,徒弟出师后便可以用弘毅国术的招牌继续拓展业务。龚桂冬认为,“现在,黄埔醒狮行业有八成是我们的团队。”小众行业在早期应当以推广为主,避免“小散弱”,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共同把品牌做大。
随着醒狮运动的商业化发展,产业链向上游蔓延,还带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自2018年起,由彩扎(广州狮头)市级传承人陈金明担任首席工艺师,广州南国醒狮贸易发展公司先后在河源、清远等地的乡村设立了一批醒狮扎作车间,年产近3万头醒狮,产值超3000万元,其中约七成外销,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增长尤为迅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非遗学院执行院长桂元龙认为,相比龙舟等其他非遗体育项目,醒狮的商业化基础较好。它不与特定日期绑定,无论是节庆活动还是商铺开张,都有商演的机会,与文旅结合的能力也不错。
但即便如此,醒狮的商业化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龚桂冬透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亏本运营。这种状态直到2020年前后才开始转变。”
2024年,“英歌舞”意外破圈,抖音全年相关话题量超200亿次。潮汕地区迅速将相关元素引入景区,甚至打造出英歌舞机器人,使得热度在今年春节继续攀升,流量效应进一步释放,共计为潮州、汕头、揭阳三地吸引游客近1300万人次。
在佛山禅城,全区已有醒狮运动团体53队,从业人员超2000人,醒狮制作企业也汇聚于此。以醒狮产业体系为基础,禅城南庄落地了巨型机械醒狮超级IP,打造“全球醒狮第一街”,以进一步深挖醒狮相关的展演、文创展销、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潜力。
有了这些成功的先例,走向商业化的醒狮,能否找到与广州的文旅、潮流、风貌相融的契合点呢?
长岭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样本。包括水西社区在内,街道9个社区的狮队均已组建完成。近年来,长岭街道成立了醒狮复兴工作组,每年可申请到一批财政资金用于醒狮推广。以水西醒狮队为例,每年能够获得约10万元的政府补贴资金,用于公益演出、培训支出以及道具更新等方面。
钟伟光解释说,长岭是一个2019年才成立的新街道,与广州其他地区相比,其工商业并不突出,整体以宜居为主。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与定位使得当地更加重视非遗的留存。“特别是这两年旧村改造越来越快,我们希望醒狮能提升长岭的文化辨识度。”
也是从2019年起,长岭每年面向来穗人员子女提供公益的醒狮培训。“到今天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学员也从首期的50余人增长到最新一期的200多人。”钟伟光认为,醒狮毛茸茸的外观、喜庆的锣鼓以及较低的入学门槛,使其天然具有“亲民”的特点。
2021年,长岭开设广东首条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后,醒狮表演又融入了景区。两年后,长岭醒狮文化馆开馆,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览、研学。

事实上,非遗“三进”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早已成为保护工作的思路。在醒狮进景区方面,融创、正佳、长隆等地方都出现过醒狮的身影;在进校园方面,龚桂冬早在2010年便开始推进相关项目。据他介绍,项目按照“宫校”合作的模式推进,“少年宫出钱、学校出人、我们出技术”。目前,黄埔区香雪小学也成为全国唯一个将醒狮搬进体育课的学校。
此外,近年来,以醒狮为主题的音乐剧、影视动漫等文艺作品也提升了醒狮的知名度。这些充满岭南特色的草根故事,都成为了城市IP的有机组成部分。
身后有政府产业基金支持的《雄狮少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电影的票房不及预期,但其撬动的新媒体、文旅演艺和衍生品市场总计超40亿元。特别是去年同名音乐剧先后登陆约20城,80场次几乎场场爆满。广州易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海明透露,电影上映后,2022年上半年,“舞狮”这一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从一天几千增长到70多万,广东舞狮表演、比赛半年内增加了约4倍。
日渐临近的十五运将为醒狮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契机。据悉,舞龙舞狮已被列入“十五运”展演类群众赛事活动项目。龚桂冬透露,醒狮计划被搬上开幕式,目前初步确定将有100头醒狮登台表演。
本文详细阐述了岭南醒狮的发展现状、历程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它曾在城市化进程中陷入困境,但随着政策支持和各方努力,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在商业化方面虽有进展但仍面临困难,不过通过长岭等地的成功实践以及文艺作品的推动,醒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即将到来的十五运为醒狮提供了更大的展示平台,有望进一步促进其发展。
原创文章,作者:东京迎荷,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