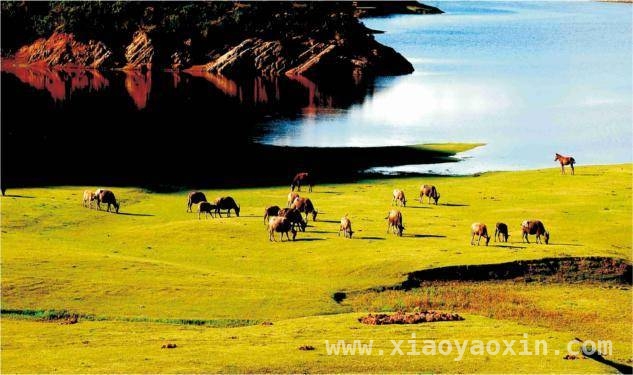本文围绕小说《803》展开,介绍了其与“三线建设”的关联,剖析了书中蕴含的好奇心、地方感和地理想象,阐述了人和景观的复调关系,引导读者从地理和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作品的内涵。
有这样一座特殊的基地,它宛如山中的一座小岛,又似能随时升空的潜艇。《803》这部作品,从书名便能看出,它与那已经逐渐失落的工业记忆紧密相连。一个简单的数字代号,背后承载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关联着一批迁徙的人,更对应着一个充满随机性的地点。
2024年正值“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各类研讨会议和纪念活动纷纷开展,大家都在努力探寻和彰显曾经工业辉煌留下的旧日痕迹,试图从中找到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必由之路。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几部“三线建设”口述实录,将成百上千人的人生进行了浓缩,这里面有成百上千份对自己人生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有光荣与自豪,也有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坦然接受的过往。《803》的故事起点和存在原因都和“三线建设”相关,但它与那些大规模的历史记忆以及以“三线”地区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
虽然一项海军潜望镜任务的代号为《803》确定了名称,一座“三线”基地的兴衰为故事划定了基本框架,但实际上,它更关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试图描绘个人与文明、时间与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交错关系。《803》就像是人和景观的复调乐章,在故事里,景观(包括空间和地方)并非只是简单的背景,而是如同鲜活的角色一般。同时,它也聚焦于边界、区隔、移动、轨迹等地理学中常见的话题,并且保留着人类最本初的地理好奇心,涉及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想象。以一种关注景观、感受地理想象的方式去阅读《803》,能够引发读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入思考,体会到地理为故事带来的宽广基调。

《803》由胡凌云创作,于2024年12月由乐府文化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好奇心、地方感和地理想象
《803》的故事有一个确切的开端——上海光学仪器厂内迁贵阳新添寨建立的新厂,这便是主人公船长口中的“基地”。故事开篇以少年船长的视角展开,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岛仿佛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体系。那外墙刷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无尘恒温大楼,不仅拥有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装配工,在少年眼中,它还具备制造神秘武器的强大力量。在这座与周围环境截然不同的人工岛上出生,意味着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和观察“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努力去理解有形和无形的边界。无论是围墙、河流,还是人为划定的界限,亦或是已经消逝的人类景观,无论这些地物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人物的生命始终与它们紧密交织,并且因它们的存在而不断推进。
少年船长对凡尔纳作品的热爱,是《803》全书地理好奇心的源头。在那个封闭的小世界里,孩子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探险,绘制出眼中世界的想象地图,又凭借真实的地图在脑海中构建出想象的地貌景观。这一切都带着人类最原始的地理好奇心,也是凡尔纳的世界和地理学探险时代的精髓所在。而且,这种好奇心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增长、生活半径的扩大以及故事推移至成年人的世界而消失。
当然,随着视野的改变,心理感知地图必然会发生变化。幼儿时期,家就是母亲的膝上,母亲的身体就是生命中最永恒的景观;儿童沿着河流一天天长大,他们探寻漆黑的山洞,聆听石子落底时那深不可测的声音。青年时期,经过的立交桥成为新世界的入口,是“现在向未来推进的边界”,桥名似乎也暗示着“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维度”。离开家乡后再回望和想象家乡,由于心理上空间尺度的变化,感知地图在比例尺缩小的同时,由平面变为立体。想象中的溯源之旅,仿佛能借助原子能汽艇驶过大洋大江,家乡也变成了立体地球上的一个小点。
最初的地理好奇心也会因成长和视野的改变而产生新的层次。无论是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通道,还是人类文明在景观中留下的痕迹,亦或是对航天飞机联通未来的想象,地理好奇心推动着文本中时间与空间的层次感,将个体与过去和未来紧密相连。因为过去的时光和人类的力量早已融入景观之中,而对未来世界环境的想象往往源于对技术的信念或失望。
《803》存在的根源在于一个在地理意义上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国家决策,以及看似微不足道却决定了千百人命运的选址,还有因此产生的大批人口毫无选择的迁移。这意味着故事基因中蕴含着浓厚的地理性。所以,书中的人物就像地理信息中的矢量数据一样,自带坐标和方向。人物的坐标比地理事物的坐标更为复杂,它可以是籍贯、位置、居所,同时也离不开地方认同以及地方依恋的界定。人物的方向指明了他们的轨迹,这些轨迹也因人对地方的心理感受和情感而产生。在这里,坐标和方向都体现着人地关系。船长父母的方向源自进山的铁轨和对家乡的思念,与父母同代的大批上海人则将对东方的向往遗传给了子女。人物的坐标和方向在故事开篇就划定了小世界中无形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物的移动和轨迹为故事构建了骨架。或者说,《803》中的人物因其内含的矢量信息而存在。作为故事主线的船长轨迹采用离散叙事的方式,天然地关注迁徙、位置标定以及在陌生景观中与熟悉事物的相遇。对其他人物轨迹的描绘以船长的视角进行,它们展现了小世界被打破、移动成为目的之后的种种可能性。这些轨迹是对故事本源的回应,故事中船长对它们的观察与回忆是对集体记忆的一种切片,这也呼应了《803》作为文学作品的一层意义——作者以一种声音、一种叙述对“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进行回应,更自由地处理传统历史书写中不在意或难以触及的细节,虽然不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的,但也能以某种方式抵达真实。
《803》的原点是“备战、备荒”的时代需求和“靠山、分散、进洞”的技术单位。少年时代的船长曾因“冷战”的氛围和盛行的“核冬天”概念,想象科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科技在《803》中是一个重要元素,它的探索性与地理好奇心相互融合,既能造成环境灾难,也能提供末日的出路以及梳理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这里,《803》中最模糊的一条界限可以引发有关文学内涵的思考——文学所涵盖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否和科学有着明确的界限?科学技术在文学中的表达,是否只有既定的途径,归属科学文艺或是类型小说。当绒线结编织技巧和《国际航空》并置时,我们能看到界限在各种层面上的消融,它们存在于一个文学文本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书中所保存的科技,无论是探索未知、雄心破灭,还是具有十足的毁灭性,同样都是人类的生命故事。

人和景观的复调
人在国土的南北东西之间穿梭,跨越大洲大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游荡或急速前行,人的方向和轨迹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当人穿过景观时,景观本身也成为了故事的线索。山川、河流、地层、城市形态、古代文明遗迹,都因时间的塑造而呈现出动态的特性。《803》中的重要元素——时间(也是地理学的要素),因景观的动态化而变得有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故事中的景观以层叠的形态出现,同时被环境演化、人类的记忆以及个人的回忆和想象所塑造,它们因此具有了生命。
在人与景观的交互过程中,将景观视为有生命之物源于人对大地天然的依恋。更进一步,《803》在隐喻、比较和想象中模糊了人与景观的界限,人可以成为景观的外延。当人物的地理属性极其鲜明时,便化身为地方本身,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地方感的映射。
采用离散叙事的《803》有着悼亡与追忆的需求,这使得回答“从何处而来”这一问题、定位个体生命和追溯家族历史具有了多重意义。我们常常会随着文本感受到南方雨雾带来的湿冷气息,时而进入一个由松软土壤和超凡力量构筑的位于生与死之间的连续空间。我们也能够理解文本中重复的回忆、层叠的景观(如果把它们绘制成剖面图,看到的一定不是平直的层理,而是褶皱和断层)。景观的生命性更因处理生与死的问题而变得鲜活,因为景观本身是承载记忆和情感的容器。人与景观也更加难以区分彼此,人所经历的景观被写入身体内部,或是穿过生命本身。
景观使得个体生命的定位成为可能,回溯过去需要依据河的流向和山的位置,它们能够定位的不仅是现实的生命,还有那逝去的和想象的。童年的未解之谜,可能与不知源头和流向的小河有关,与记忆中深藏的铁轨与山洞有关,与不知是蜃景还是想象的雪山有关。长大后,也许有机会解开这些谜团,也许只能将它们视作消失的秘境。这预示着,无论是追溯家族的记忆,还是回望古代文明遗留下的痕迹,即便进行巨细靡遗的描摹,也只能捕捉到真实时代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使我们能够接近重建的景观,即便那景观可能是水底一弯捞不起的月。当触及水面时泛起的波澜,便是读者能在其间与真实产生的一点共鸣。
本文详细剖析了小说《803》,它与“三线建设”紧密相连,书中充满了地理好奇心、地方感和地理想象,展现了人和景观的复调关系。通过对书中故事、人物和景观的分析,揭示了个体与历史、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引导读者从多个角度去思考作品的深刻内涵。
原创文章,作者:宫古千凡,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26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