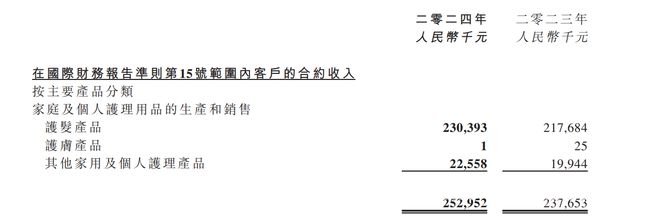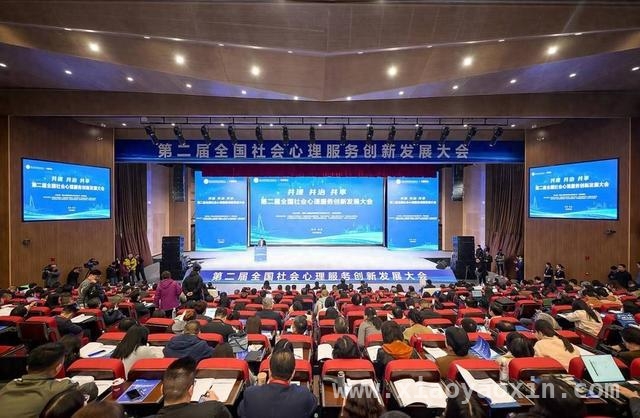本文围绕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展开,作者结合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讲课的经历,讲述了学生对这首诗的讨论,进而深入剖析诗中所蕴含的幸福含义、海子创作此诗时的心境以及诗背后隐藏的不安定因素等内容。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由张新颖所著,于2024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海子众多的诗作中,《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或许是流传最广的一首。有人为它谱曲并唱成了歌,它还被选入了几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甚至有些读者只读了海子的这一首诗。
在这个秋季,我于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讲授“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课程,其中专门安排了一次课来讲海子的诗。原本在教学大纲里,我主要计划讲解《麦地》《春天,十个海子》等作品。然而,在上课前一周,我突然想到让助教找来《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分发给选课的学生。当时我的想法是,这首诗风格简单、明朗且亲切,或许能帮助学生拉近与诗人的距离。
原本我只是打算让大家简单读一读这首诗,然后就过渡到其他作品。可没想到,这首诗引发了一场十分有意思的讨论。有一位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美国学生Anne Rebull提出疑问:这个自杀的诗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或者换个角度问,写出这样诗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要知道,这首诗创作于1989年1月13日,仅仅两个月后的3月26日,海子就在山海关卧轨离世。还有一位在中国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女生问道:为什么他所定义的幸福里没有做老板、赚大钱这些内容呢?
学生们的疑问也让我陷入了思考。难道这首诗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通俗”?是不是我们对这首诗的态度过于草率了呢?
幸福,其实就是“尘世”的幸福
这首诗深受人们喜爱,大家喜欢它开阔而明净的意境,喜欢它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境界中散发出来的那股暖融融、清新的幸福气息,也喜欢它对幸福的单纯、基本的界定。如今,人们的幸福意识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微且充满装饰性,对幸福的追求越是用力,反而离幸福越远。其实,幸福也许就藏在那些简单、普通却又基本的事情当中,或者说,那些事情本身就是幸福,比如“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与别人愉快相处,“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向“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小森林 夏秋篇》(2014)剧照。
“粮食和蔬菜”作为关心的对象、幸福的元素出现在诗中,对于熟悉海子诗的人来说,这感觉非常自然。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土地上生长的食物的大类,并非具体的、特殊的物种,既不是海子诗中一再出现的麦子和麦地,更不是那充满痛苦质问的“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答复》)中的麦地。“粮食和蔬菜”是平凡、普通、中性的大类,而幸福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没有尖锐性、能够包容众多东西的大类,不需要与个人经验、意识、情感紧密相连的独特具体物种。虽然“粮食和蔬菜”确实是海子关心的事物,但在这里,他把独属于自己的意识和感受暂时搁置了起来。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这体现了幸福的可沟通性和可分享性。幸福是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而且说出来之后,其他人能够立刻明白和理解;幸福也是可以传递的,在传递过程中,它不但不会损耗,反而会增加。传递幸福不仅能让别人感受到幸福,也会让传递者自身更加幸福。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幸福是可以说出来、可以传递的呢?显然,那些独属于个人的意识和感受、具有精神尖锐性和排斥性的东西,在沟通和分享时会遇到困难。海子在诗中所表达的并非此类。列夫·托尔斯泰用“幸福的家庭个个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来开启一部巨著,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不幸具有个性,而幸福没有个性,幸福是相似的。
接下来,海子说得更加明确了,幸福其实就是“尘世”的幸福。他对陌生人的祝福,“愿他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他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他‘在尘世获得幸福’”,这虽然像是祝福的套语,甚至可以说是滥调,但幸福不就是如此“通俗”吗?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幸福,不正是这样的吗?

《海边的曼彻斯特》(2016)剧照。
海子祝愿所有人都能获得“尘世”的幸福,而他自己,只想要其中的一点点:“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决定做一个幸福的人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个简洁干脆的句子,仿佛在说,做一个幸福的人仅仅是一个决定,只要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可以了,那就“从明天起”开始吧。
是什么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从诗的表面,我们很难找到足够的线索。不过,“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这句话,隐含着重要的信息,尽管信息并不明确。“幸福的闪电”究竟是什么呢?它可能是在他内心深处突然产生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瞬间照亮了他精神世界的黑暗;也可能是从外部奇迹般降临到他身上的,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一下子照亮了他灰暗的生活;又或者,这“幸福的闪电”根本就没有发生,只是他内心渴望被这样的“幸福的闪电”击中。不管怎样,这个“幸福的闪电”(哪怕只是想象中的)让他感受到了幸福,并且决定将这份幸福传递出去,决定做一个幸福的人。
这首诗给人带来的清新之感,正是源于这个决定。有了这个决定,就仿佛与过去彻底决裂,“从明天开始”,他将拥有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新的自我会在新的世界里去做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显然,这是一种和顺、令人愉悦的关系。
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的建立看作是个人向世界妥协的结果,而应该说,是先有了一个新的自我,然后才有了一个新的世界。“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这个命名的行为,是一种原初的创造行为,是让一个世界得以开启的行为,是赋予这个世界某种特质的行为。就好像在这之前,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没有名字,而“我”给它们取了“温暖的名字”,它们就变得“温暖”了。

《小森林 夏秋篇》(2014)剧照。
从诗中来看,“我”似乎是温顺、亲切的,没有棱角和锋芒,没有挑战性,也没有质问的痛苦和激愤,他与世界的关系似乎改善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世界并非现实世界,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喂马,劈柴”到“周游世界”,从“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在这样的世界里,他自然无须剑拔弩张。只要他决定做一个幸福的人,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有“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他所期待的那个新的自我和新的世界,何时才会出现呢?答案似乎很简单,就在眼前,就是“明天”。
可是,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呢?为什么不从今天、从现在就开始呢?他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的历史要从“明天”才开始算起;他的现在,似乎也不存在。
然而,我们还是忍不住会问:现在的“我”,在“明天”到来之前的“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处于一个怎样的世界中?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些问题一旦被提出,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并非一个幸福的人。他没有和每一个亲人通信,他不善于沟通,也没有可以传递和分享的幸福告知亲人。他被困在了自己的精神困境里,也不可能通过重新命名世界来改变世界。
没过多久,在他自杀前十几天写的诗里,他想象春天里十个海子复活;然而,就在这个“做一个幸福的人”所向往的“春暖花开”的季节,依然有“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长久地沉睡——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这首诗本身也许是“反着说”
在《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那令人产生幸福想象的表面之下,其实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隐藏着威胁着这个美丽世界的因素。反向阅读这首诗,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这些因素。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触及甚至追究这些因素呢?为什么要这么扫兴呢?为什么要逆着这首诗去读,而不是顺着它去读呢?
也许海子这首诗本身就是“反着说”的,如果我们“反着读”,说不定恰好就顺正了。
为什么他会在自杀前不久写下这样一首诗呢?有一位朋友在和我通信时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几年前,我编选的《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她认为应该把海子的这首诗选入其中。现在我想起来,便写信询问她对这首诗的具体看法。在谈到自杀和“幸福之诗”的关系时,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理,在此抄录如下:“首先,海子当然知道,或者有时也会羡慕尘世的幸福;不过我想他并没有得到。其次,是不是在那段时间,他的精神压力已经非常大,所以写了这首诗,就像一份保证书,或者一种心理暗示,为自己找一个短暂的出口。也许只有当诗人自身状态和写出来的文字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向拉力时,那些美好而空洞的祝福——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才能够被理解和接纳。在祝福世界的时候,他也祝福了自己。也许他想要的是一种解脱。这就像一首在绝望的时候唱起的赞美诗,如果其中有绝望,那一定是彻底的绝望了。”

《海边的曼彻斯特》(2016)剧照。
不过,对于“绝望的时候唱起的赞美诗”,我们既可以把焦点放在“绝望”上,也可以放在“赞美诗”上。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顺着这首诗去读,从正面去接受这首诗,承认这个明媚的世界和幸福的许诺。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做一个幸福的人仅仅是一个决定,如果我决定做一个幸福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海子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他太坚信自己是那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了;但这或许不应该妨碍海子诗的广大普通读者去相信一个决定的力量,去尝试实现这个决定。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试一试吗?
给自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尝试吗?
海子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诗会如此广泛地流传,甚至读他诗的声音会回响在“熟麦的卷发”“海水的眼睛”之间。他曾经想象在收麦时节,月光普照下,“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他还说过,“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麦地》)。这些内容,也是我课堂上学生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从学校走到密歇根湖边,只需十几分钟的路程。面朝那望不到头的蓝色水域,我常常会恍惚觉得这不是湖,而是海。这种恍惚似乎也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五大湖相互连接,后来我了解到,地理学家们称其为“北美地中海”,或者是“内陆淡水海”。实际上,即使是被称为“淡水海”的湖,与真正的海还是有所不同,比如这里缺少大海的潮腥味。我不知道海子有没有见过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长时间在海边生活过。我忽然想到,当海子想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他的想象里,有没有大海的潮腥味呢?
本文围绕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展开多维度探讨,通过课堂上学生的讨论引出对诗中幸福含义的解读,分析了海子创作时的心境以及诗背后隐藏的精神困境。指出诗可能是“反着说”的,同时也鼓励读者从正面接受诗中的幸福许诺,相信做幸福的人的决定的力量。
原创文章,作者:宫古千凡,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7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