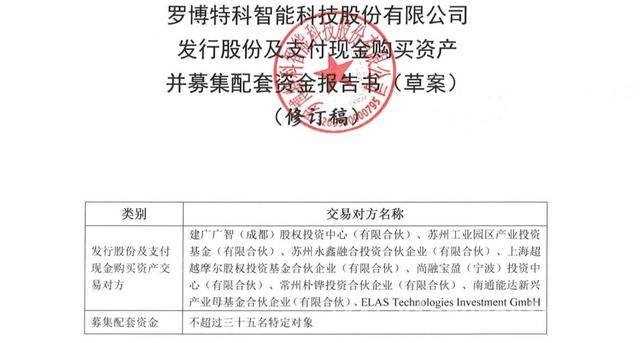本文聚焦于2025年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国大学的变革,围绕“大学2025”专题,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在人文领域学术研究以及高等教育人文学科中的作用与局限,同时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界定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思考。
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大学迎来了2025年。这一年,注定是充满变革的一年。中国大学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是凭借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还是在延误中错失转型机遇,一场新的征途已然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给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大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学科建设,又会给创新人才培养带来哪些启示?澎湃新闻特别推出“大学2025”专题,旨在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大学所发生的变革。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马一浮书院兼任研究员彭国翔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AI或许能够协助研究者快速检索已有研究,并提供相关资料。然而,它还无法替代学者在选题策划与问题意识方面的独立思考。在个性化表达上,AI也难以取代真正作为“人”的学者。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尤其是大学文科教学,其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做简单的文案工作,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教养,塑造他们的人格,而这显然不是AI能够做到的。
澎湃新闻近期策划的“大学2025”专题报道,聚焦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彭国翔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专业训练出发,以“人文与AI”为主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主要想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与AI的关系;二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与AI的关系。当然,这两个问题都包含着许多进一步的问题,他目前只能就自己想到的几点略作阐述。
彭国翔认为,学术研究是高校教师从事教学的根本。如果教师不能在学术上不断自我更新,建立新知识、提炼新思想,就无法向学生讲授新知与新思。老师自己不做研究,又拿什么去教学生呢?总不能日复一日地讲授陈旧的知识。因此,他首先探讨了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与AI的关系。
首先,AI对人文学术研究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E考据时代”的概念,这里的“E”代表“electronic”。我们知道,“考据”需要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过去,学者进行一项研究、撰写一本书,需要一个人查阅卷帙浩繁的资料,制作大量的卡片。而如今,随着数据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我们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分类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所谓“E考据时代”,就是利用“数字化”(英文叫“digital”)的便利,迅速检索大量的资料。
无论是国内的DeepSeek,还是海外的ChatGPT,都具备强大的资料检索功能。尽管有时需要辨别资料的真伪,但它们能将以前相关的资料以及网上能找到的数据都提供给研究者。这对于人文研究来说,至少在资料汇集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的严耕望先生,以勤奋治学著称。他在治史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史料、制作卡片,写出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等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的坚实巨著。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相信数字化工具的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更快地完成史料搜集工作,从而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其他研究。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AI的局限性。目前来看,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选题方面。在人文研究中,选题至关重要,它决定了研究的学术价值。AI或许可以协助研究者快速检索已有研究并提供相关资料,但它无法替代学者在选题策划与问题意识方面的独立思考。比如,哪些题目有价值,哪些题目还未被研究过,哪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深入,这些问题AI很难给出答案。
其次,在学术写作方面。与理、工、农、医类的学术写作不同,人文领域的学术作品往往更能体现作者个人的风格。我们阅读不同作者的人文作品,常常能透过文字看到作者本人。作者的品味、文气、语势乃至个性,都会在其文字中得以体现。
彭国翔曾亲身经历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评审一篇博士论文,采用的是双向匿名评审方式,他只知道作者所在的大学,并不了解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评审意见出自何人之手。论文作者收到意见后,想请朋友帮忙看看如何根据审查人的意见修改,结果找到了彭国翔曾经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现在是学术期刊的编辑,他看了意见后主动询问彭国翔:“彭老师,这是不是您写的意见?”彭国翔十分惊讶,问他是如何推测出来的。学生回答说:“我一看,就觉得太像您的风格了。”这说明,在人文学术写作中,个人色彩非常浓厚。而如果是AI或者各种工具生成的文字,作者的个人特色,如品味、风格、文气、语势等,可能都会被磨灭。
曾经有朋友尝试用DeepSeek生成诗歌,感觉效果不错,甚至还尝试让它仿照某位诗人的文风创作一首诗,它也能大致做到。初看之下,这种AI生成的仿作似乎结构工整、辞藻得体,但仔细品味,与作者本人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差异。这表明,在个性化表达方面,AI仍然难以取代真正的学者。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种文体叫“馆阁体”(指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考场通用字体),风格四平八稳。也许AI可以生成类似“馆阁体”的文字。但人文学术写作不仅关乎内容,不同作者作为“人”的差异,会自然地在风格、品味、文气和语势方面表现出不同。如果人文领域的研究者使用AI进行写作,可能会导致文本的个性化表达消失,最终形成一种类似于“馆阁体”的标准化学术表达,使文章虽然工整严谨,但缺乏学者个人独特的风格和思想烙印。
彭国翔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与AI的关系,即如何看待AI在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利用AI可以快速搜集到很多资料,在撰写简单的文案、新闻稿、宣传稿时,AI可以提供参考模板。然而,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或者说大学文科教学,其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做简单的文案工作,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教养,塑造他们的人格,而这显然不是AI能够做到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AI可以帮助学生写文章,不仅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风格的“馆阁体”问题,还可能引发诚信问题。诚信问题不仅关乎学术,更关乎人格。试想,如果教师让学生写文章,学生直接让AI生成,这样的文章质量如何?能否反映学生真实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水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这不仅是AI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其危害。对于学生的人文教养来说,这显然不是好事,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界需要警惕和应对的问题。
因此,对于大学的人文教育来说,教师在教学时需要考虑如何让学生既能充分利用AI的便利,又能避免其局限性,尤其是危害。
最后,彭国翔指出,当我们讨论“人文与AI”时,似乎已经默认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然而,这一前提本身值得进一步思考。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如何界定AI的本质?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按照前面的讨论,基本上是把AI理解为一种便利的工具。然而,对于AI的理解可能不止于此。现在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将来会控制人类的讨论,如果是那样的人工智能,就不仅仅是一种便利的工具了。这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它是否可以有自主意识?如果有了自主意识,它就不一定完全听从人类的指挥,不再只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基于把AI当成工具,即使它很高级、很发达,也是为人类服务的。但如果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更进一步,如果AI不仅有自主意识,还有自己的情感、意志,那么这种AI就与人类相差无几了。彭国翔曾将这种AI称为“类人类”。当这种AI与人类相处时,就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了,整个人类如何与之共生并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也在被讨论,彭国翔以前也写过文章《人工智能最终一定是人类的威胁吗——一个儒家的视角》(《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5期),从儒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人工智能问题。
如果是具有自主意识、情感和意志的人工智能,就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不同了。现在各个领域都密切关注人工智能,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是在什么意义上的。
总之,前面讨论的两个问题,都是基于目前媒体和大众的理解,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可以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工具。这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然而,如果人工智能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甚至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到来,还不确定。而一旦到来,我们面临的将是全新的问题。虽然这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因为非常重要,所以必须提及。

设计:祝碧晨
本文围绕2025年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国大学的变革展开,探讨了人工智能在人文领域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人文学科中的作用与局限。AI在资料汇集方面对人文学术研究有帮助,但在选题策划、个性化表达等方面存在局限。在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中,AI虽能提供资料参考,但无法培养学生的人文教养和人格,还可能引发诚信问题。此外,文章还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界定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思考,提醒人们关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主意识、情感和意志等不同层面的问题。
原创文章,作者:甜雅mio,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103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