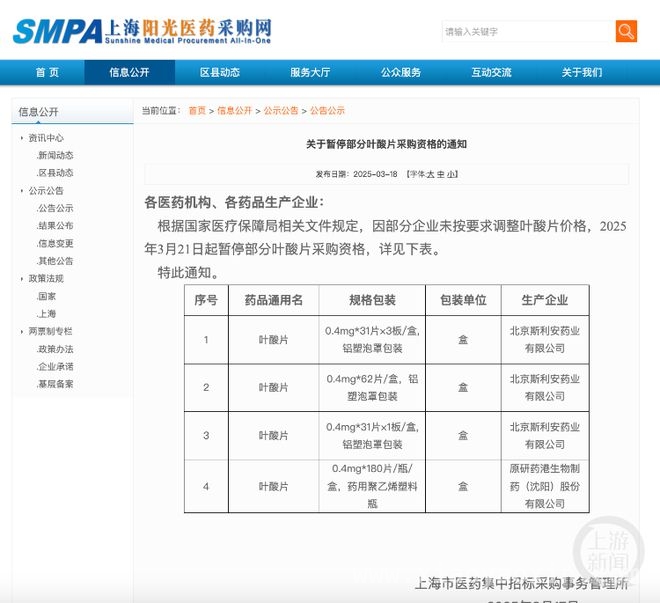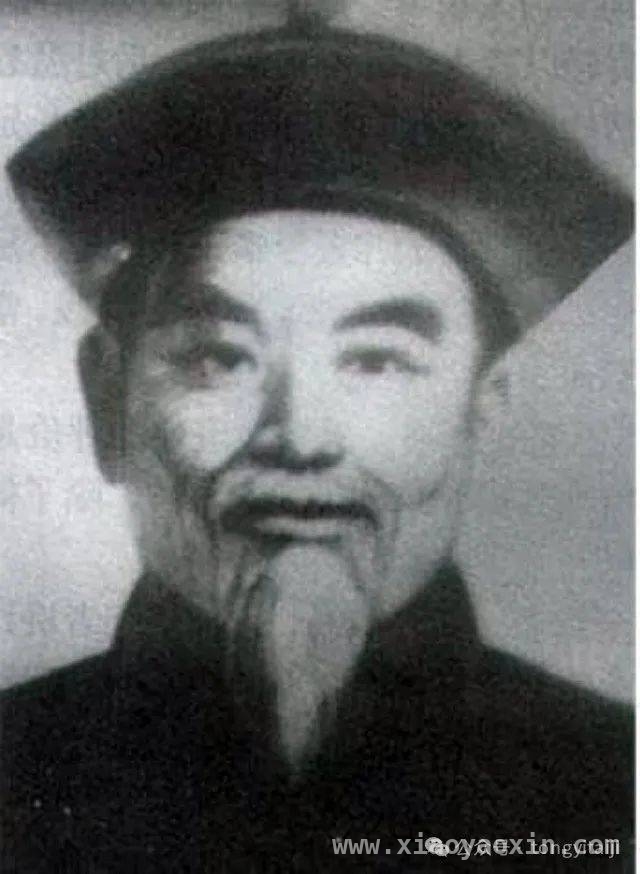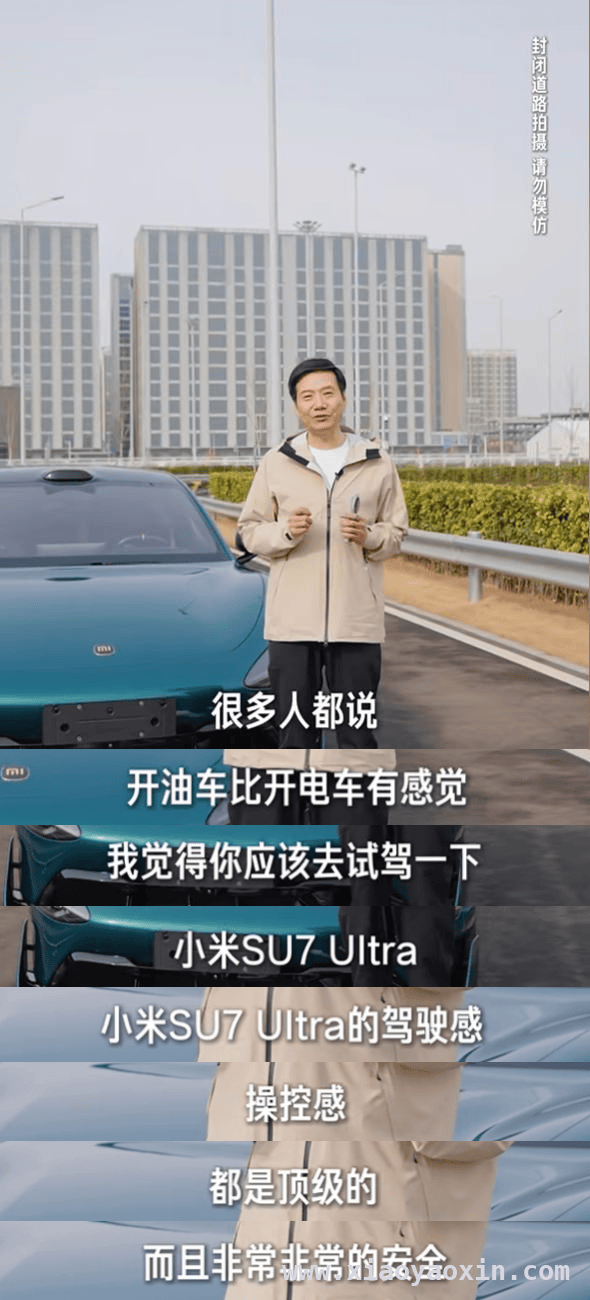本文聚焦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主题,阐述了其概念,指出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虽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但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多种实现途径,包括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精深加工等,以推动“两山”理念的转化。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在严格守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把良好生态环境所蕴含的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一系列难题,但各地依据自身生态禀赋和发展条件,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努力攻克这些难关。

在贵州省龙里县颐光山林油茶生态园,村民们正忙着搬运油茶树苗。当地逐步建设发展成为以油茶种植为主,绿化苗木、精品水果、林下养殖等为辅的生态园。这既解决了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问题,又让千亩荒山变成了青山(2025年3月11日摄)。
面临五大挑战
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当前,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存在五大挑战,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制度层面。
生态产品生产供给不够充分。随着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断增加,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强烈,从“盼温饱”转变为“盼环保”,从“求生存”转变为“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实践中,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主要通过原生态、绿色、有机等品牌认证形式提升价值,然而却存在规模小、市场散、品牌乱、竞争力弱等问题,经营开发水平较低。生态产品供给地区大多基础条件薄弱,生态产业仍集中在初级加工和旅游资源开发等初级阶段,基础设施和配套支撑体系不完善,价值实现难度较大。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冬认为,在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亟需拓展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其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收益分配不尽合理。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应充分尊重产权主体地位,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生态保护地区的原住民因保护生态而丧失部分发展机会,理应在收益分配中得到更多照顾和倾斜,收益也应更多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
现实中存在生态环境保护者未获得合理回报、受益者未支付足够费用、破坏者未付出相应代价、受害者未获得应有赔偿等情况。生态产品受益主体不明确,产权边界模糊、所有者缺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收益分配不均。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规划协调处处长曹利远认为,涉及集体资产的收益应用于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涉及个人资产的应兑付给个人,确保收益共享,畅通“两山”转化路径。
生态产品交换基础待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交换的基础在于商品的价值相等,需构建合理的价值决定机制和定价体系。既要维持生态产品的规模化再生产,也要保障农民的基础性地位和合法权益。
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不强,关键参数差异大,难以获得普遍认可。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面临困难,各领域试点多为单项推进,难以适应系统高效推进改革的需求。资源环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生态产品消费潜力未完全释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实践中生态产品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存在以下问题:生态产品交易中心不健全,宣传推介力度有限;供给方与需求方对接不精准,资源方与投资方合作不畅通;偏远地区的生态产品受运输时效和物流成本影响,价值难以实现;绿色金融对生态旅游等产业的支持力度有限,行业规模难以做大,产品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和质量追溯体系不完善,制约了产品溢价和品牌塑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不健全。2021年《意见》出台标志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完成。而分领域细化实施方案仍未完善,尚未形成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的政策合力。
此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欠缺,经济发展与生态产品总值双评价、双考核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层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花桥村,游客们在油菜花海中踏青赏花(2025年3月16日摄)。
“打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
近年来,我国多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让“两山”理念的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生态种养提升市场竞争力。部分生态产品因生长环境具有天然性、独特性甚至稀缺性,存在较大溢价空间。一些地区借助自身独特的自然条件,采用生态种养模式发展特色产业,以此提升生态产品价值与市场竞争力。
比如贵州赤水,作为金钗石斛的主产区,凭借当地适宜的气候环境与丹霞地貌,推行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的原生态种养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推动了金钗石斛生态产业的发展,营造出“荒山转绿地,石上绽红花”的美景,还形成了防止丹霞石风化、减少水土流失的生态屏障,达成了拓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以及改善自然环境、修复生态的多赢局面。
黑龙江宁安渤海镇的“石板大米”同样如此。其生长在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台地,火山灰与腐殖土构成的肥沃土壤富含矿物质和有机质,镜泊湖的优质水源用于灌溉。当地除坚持绿色种植外,还采用物理方式杀虫、稻田养鸭除草、追施农家肥,并借助手机客户端监控系统实现水稻种植到收割的全程可视化监测,确保质量安全可追溯。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生态种养方式与安全追溯模式,提升了农产品的生态、经济价值以及口碑信誉度,促使农户持续采用生态种养模式发展绿色农业。
激活传统深耕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作为绿色环保、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业态,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的重要路径。资源禀赋良好的地区着力打造集旅游、文化、康养、休闲、科教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模式。
发展生态旅游,不仅需要良好的自然本底,还需深入挖掘多元生态价值,激活历史文化传统,赋予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可针对观光旅游与康养休闲需求,开发相应服务与产品,并通过研学实践等形式,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教功能。
云南省绿春县便是典型例子。此地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其中哈尼族的多声部民歌、长街宴、棕扇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绿春通过举办哈尼长街古宴、玛玉茶开采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哈尼族的民俗风情,有效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精深加工拓展产业价值链。生态产品的原材料市场价格普遍偏低,群众单纯依靠生产和售卖原材料,经济收入有限。借助先进技术推动生态产品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全产业链方向迈进,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
福建南平素有“中国笋都竹乡”美誉,当地依托竹资源富集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笋竹精深加工。产品从原竹销售和粗加工的竹拉丝、竹条、竹胶合板,拓展到精深加工的竹餐具、竹家具、重组竹板材、竹工艺品等。并且利用竹边角料生产竹刨花板和活性炭,构建起全竹利用产业链。此外,南平把握“以竹代塑”“以竹代木”的发展契机,发挥竹子绿色、低碳、可降解、可再生、生长周期短的特性,积极研发各类竹制品。竹制品加工业的发展,反过来激励和推动第一产业的提升。做好竹林培育工作,也为第三产业围绕竹资源、竹产业和竹文化开展生态旅游积累了丰富资源,最终实现三次产业联动发展。
另辟蹊径打造新优势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除了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极寒气候也能成为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发展资源。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自身区位、资源和气候优势,将寒地测试产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方向之一。在2022年至2023年的寒地测试季,多家车企及试验人员入驻当地,带动了旅游、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2024年年初,39家车企和500多名技术专家齐聚漠河红河谷测试基地,对新能源汽车进行极寒性能测试。
培育主体助力高质量发展。一些地区对废弃矿山、工业遗址、传统村落等进行生态修复,并与生态产业有机结合,使其成为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新业态。
以北京市房山区曹家坊矿区为例,由于历史上长期开采,这里的自然生态系统曾严重退化。近年来,当地科学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结合修复成果,积极探索生态修复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推动传统采矿业向绿色经济转型。曾经的废弃矿山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绿水青山蓝天、京西花上人间”的亮丽景区,形成了“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本文全面分析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生产供给不充分、收益分配不合理、交换基础不完善、消费潜力未释放和制度体系不健全等五大挑战,同时介绍了各地通过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精深加工、打造新优势产业和培育主体等多种途径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这表明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虽困难重重,但也在积极寻求突破,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推动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原创文章,作者:半荷mio,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52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