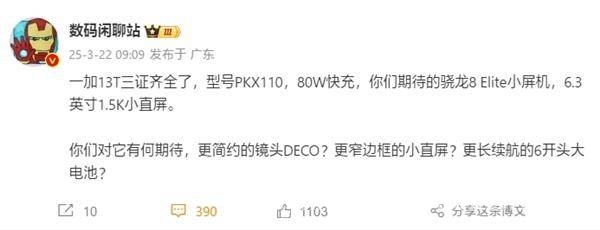荀子在稷下学宫的经历,包括他两次成为祭酒期间齐国的兴衰变化,以及他与屈原的渊源。荀子在稷下学宫发挥重要作用,多次预言成真,其治国理念却未被齐闵王采纳致齐国灭亡,后又助力齐襄王复兴学宫。同时,文章阐述了荀子与屈原虽身处不同国家,但在人格、理想、思想等方面有诸多相似,还在文学上有着特殊缘分。

荀子屈原辞赋缘 稷下学宫复兴史
范文华
荀子重振学宫
荀子的一生,与稷下学宫紧密相连。他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成为了天下学者所追慕的学术领袖。
荀子首次荣任祭酒之时,正值齐闵王前期,齐国处于鼎盛时代。而他第二次成为祭酒,则是在齐襄王复国的时期。荀子亲身见证了齐国从繁荣昌盛走向亡国,又从亡国走向复国的沧桑巨变。
齐闵王前期,他任命荀子为祭酒,还迎娶宿瘤女为王后。那时的齐国,朝堂之上有荀子这样的圣人辅佐,宫廷之中有贤良的王后坐镇,国家的声威如日中天。然而,王后不幸去世后,齐闵王的性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一心想要恢复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荀子多次向齐闵王进献“礼义”与“王道”的治国理念,可齐闵王似乎更热衷于“武力”与“权谋”。他重用孟尝君为相国,使得权谋之风日益盛行,齐国也陷入了穷兵黩武的困境,逐渐走向了亡国的边缘。在荀子的眼中,孟尝君乃是篡位之臣。
荀子大胆地预言:孟尝君久必篡位!王安石在《孟尝君传》中也曾指出:“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以荀子为首的稷下学者,大多是诸子百家的有识之士,是能够振兴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以孟尝君为首的齐国门客,多是鸡鸣狗盗、游手好闲之徒。齐闵王重用孟尝君,让这些人鸡犬升天,真正的人才对此感到羞耻。
不久之后,荀子的预言得到了验证。齐国爆发了震惊天下的“田甲劫王”事件,刺客田甲劫持齐闵王,最终以失败告终。齐闵王大怒,下令严查幕后主谋。与此同时,齐相孟尝君连夜逃往薛城。原来,刺客田甲正是孟尝君的门客。齐闵王想起荀子的预言,立即废除了孟尝君的相国之位,开始亲自执政。然而,他并没有从“用人不当”的教训中吸取经验,依然走上了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尽管齐国国力强盛,但“国虽大,好战必亡”。在齐国灭亡之前,呈现出了一种回光返照式的辉煌。齐闵王一举灭掉了号称“千乘之国”的宋国,向南侵入楚国,占据了淮北之地;向西攻打赵、魏、韩国,在中原地区争雄;泗水一带的诸侯,如邹国与鲁国的国君纷纷俯首称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齐闵王,居功自傲,竟然妄图吞并周王室,自立为天子。
稷下学宫的有识之士纷纷劝谏齐闵王,但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大臣狐咺义正辞严地劝谏,却被斩首于檀台大路上;大臣陈举直言劝止,也被杀死在临淄东门。此时的齐国,好战成风,齐王嗜杀,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那么,荀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
荀子身为学宫祭酒、诸子领袖,直面齐王的屠刀,毅然踏着贤士的血迹,为齐国的苍生百姓登高一呼!(《荀子·王霸》)
齐闵王傲慢地问道:“寡人刚刚吞并宋国,用齐国代替周王朝,自立为天子如何?”
荀子回答道:“提倡礼义,就可以称王;树立信誉,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则必然灭亡。”
齐闵王不以为然地说:“寡人喜欢权谋。”
荀子进一步解释道:“君王如果提倡权谋,追求功利,讲究欺诈,而不发扬礼义,不维护信誉,对内不惜欺诈百姓以获取蝇头小利,对外不惜欺诈盟友以贪图大利。就像如今的齐国,敌国轻视,盟国怀疑,权谋日益盛行,国家必然江河日下,直至灭亡。”
齐闵王面带怒容地说:“君王主持国家,有何不可?”
荀子劝谏道:“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会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拥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大王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而大王您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
齐闵王听后暴怒,拍案而起:“寡人不能遵从荀先生的治国之道。您还是离开齐国吧!”
以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为了齐国竭忠尽智,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可惜,齐闵王“矜功不休”,毫不听从他们的建议,最终导致稷下学宫的诸子百家纷纷离去。其中,荀子离开齐国,前往楚国。
荀子的预言再度应验。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共同攻打齐国。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乐毅破齐,使得东方大国的威势不复存在,稷下学宫也遭到了全面的衰落。齐闵王没有听从荀子的良言,最后落得个“倒悬祖庙,抽筋而死”的悲惨结局。
七年之后,田单利用“火牛阵”大破燕军,迅速收复了齐国的七十余座城池。齐襄王回到临淄,深知要复兴齐国,必须先复兴稷下学宫。环顾当时的学者,唯有荀子在年龄、学养、人品、威望等方面最令人信服。于是,齐襄王真诚地邀请荀子返回齐国,主持复兴学术的文化大业。荀子毅然从楚国回到齐国,亲自参与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
齐襄王谦恭地礼拜荀子,问道:“请问荀先生,齐国衰落的教训是什么?”
荀子回答道:“齐闵王治理强大的齐国,不提倡礼义,不修明政治,没有统一天下的思想理论,却将精力浪费在结党营私与外交权谋上。齐王身死国亡,蒙受了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世提起暴君,就必定以齐国为借鉴。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齐闵王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
齐襄王恭敬地施礼说:“寡人愿拜荀先生为祭酒,复兴稷下,振兴齐国。”
此后,荀子在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居“列大夫”之首,第二次成为祭酒。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荀子成为了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同时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领导者。他在稷下学宫“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荀子弟子们,也在这一时期从天下四方慕名而来。
荀子与屈原
荀子与屈原,堪称战国夜空中的双子星座。荀子是赵国的思想家,屈原是楚国的诗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拥有光辉的人格、崇高的理想、爱民的初心和对艺术的追求,是战国文化史上的无双国士。
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祭酒,成为诸子百家的学术领袖。而屈原在楚国担任左徒,他明于治乱之道,善于外交辞令,在内与楚王商议国事、颁发号令,在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是楚怀王的外交重臣。屈原的外交政策是“齐楚联盟,共抗强秦”。据《稷下学史》记载,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那时正值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屈原的思想对荀况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屈原出使齐国,在与齐王约定齐楚联盟的同时,还专程到稷下学宫与荀子探讨学术,这应该是他们的首次见面。
可惜的是,楚怀王中了张仪的圈套,“闭关而绝齐”,使得屈原辛苦促成的齐楚联盟功亏一篑。后来齐闵王向南侵入楚国,占据了淮北之地。荀子也曾劝说:“敌国轻视,盟国怀疑!”这里的敌国指的是日后攻破齐国的燕国,盟国则是屈原的祖国楚国。齐闵王轻视敌国、怀疑盟国,最终导致了齐国的灭亡。由此可见,荀子非常认同屈原“齐楚联盟”的外交战略。
乐毅破齐之后,荀子来到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地方六千里”,本是最有“王霸之资”的国家。然而,楚怀王末期,政治腐败,国势颓废,屈原被放逐,奸臣当道。秦国派白起攻楚,白起水灌鄢城,淹死楚军民数十万人;火烧夷陵,焚毁了楚国的宗庙与陵墓,最终攻陷了楚国的首都——郢都。楚大夫屈原悲愤之下投汨罗江殉国。楚国因此迁都到了陈,从此一蹶不振。
楚王痛定思痛,追思屈原,向荀子请教。楚王问道:“孤王的父亲——楚怀王困死在秦国,郢都也被秦军攻破,孤王背着三位先王的灵位躲避在陈、蔡两地之间。秦国是楚国的仇敌,而楚国却不得不听从仇敌的奴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荀子回答道:“楚国以汝水、颍水作为天险,以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但是秦军一到,鄢、郢就被攻破了,就像摇落干枯的树叶一样,摧枯拉朽。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与险要的地形吗?这是因为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办法,并不是礼义之道的缘故啊。不善于运用圣王之道,楚国方圆六千里的土地也要被仇敌所奴役!”(《荀子·强国》)荀子进一步阐发这个“道”,就是“礼”,乃“强国之本,威行之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可惜楚王昏庸,未能推行荀子的“隆礼”之策。稷下的那次送别,竟成了诀别,荀子再也见不到屈原了。
齐楚联盟破碎之后,齐国首都临淄被燕国占领,楚国首都郢都也被秦国占领。这充分说明了屈原与荀子所主张的“齐楚联盟”具有多么深远的战略远见!多年之后,荀子的徒孙——贾谊(荀子弟子张苍之弟子),在渡过湘水之时,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来纪念屈原。荀子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全新体裁——赋,汉赋成为了大汉王朝四百年的文学象征。屈原是楚辞之祖,荀子是汉赋之祖。贾谊用汉赋纪念屈原,可谓情深意切。司马迁将屈原、贾谊二人合传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由此可见,荀子与屈原在文学上有着特殊的缘分。
据《屈原论稿》记载,荀况是战国末期最大的儒家,屈原吸收了荀子的学说。荀子主张“美政”(美德善政)(《荀子·儒效》),屈原也曾劝说楚怀王推行“美政”来治国安民。荀子重视修身,写了《荀子·修身》;屈原也重视道德修养,自称“独好修以为常”。荀况写《天论》,论天人之分;屈原写《天问》,对天命提出了质疑。
从“美政”追求,到“修身”素养,再到对于“天命观”的探索,荀子与屈原,真可谓是千古难遇的知音。特别是,屈原的《天问》与荀子的《天论》,很可能就是二人的唱和之作。屈原的《天问》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天地阴阳、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顽与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屈原对迷信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荀子的《天论》,几乎就是对屈原《天问》的理性解答,体现了“天行有常”的唯物思想,“应之以治则吉”的积极精神,“制天命而用之”的创新智慧,“人定胜天”的自强骨气。《天问》是诗歌,充满了质疑精神与浪漫色彩;《天论》是论文,充满了唯物思想与自强精神。这两篇经典之作,都贯穿着中华先秦文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与屈原,心心相印,这个心,正是民心。屈原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荀子·王制》中也有:“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据明代《郁离子》记载,荀子还曾登高一呼:“今三闾大夫放死于湘!王如不省,楚国危矣!”荀子向楚王发出亡国警告,更是为屈原之死而鸣不平。荀子像屈原一样,都有一颗爱民的赤诚之心。正如《辞赋之交》的歌词所唱:屈原在汨罗江畔,荀子在兰陵山头。屈原将楚辞歌罢,荀子以赋曲祭酒。辞是屈原的灵魂,赋是荀子的乡愁。哀民生之多艰,嫉浊世之隐忧。屈原,为国为民上下求索,九死犹未悔;荀子,求礼求法四海奔波,百年成白头。举世混浊不同流;水能载舟亦覆舟。乐莫乐兮新相知,相遇知音更何求?
本文围绕荀子与稷下学宫、屈原展开,详细讲述了荀子在稷下学宫的经历,他的治国理念和预言,以及齐国兴衰的过程。同时,深入探讨了荀子与屈原在思想、文学和人格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展现了他们在战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文化贡献,揭示了“齐楚联盟”战略的远见卓识以及礼义治国的重要性。
原创文章,作者:半荷mio,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8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