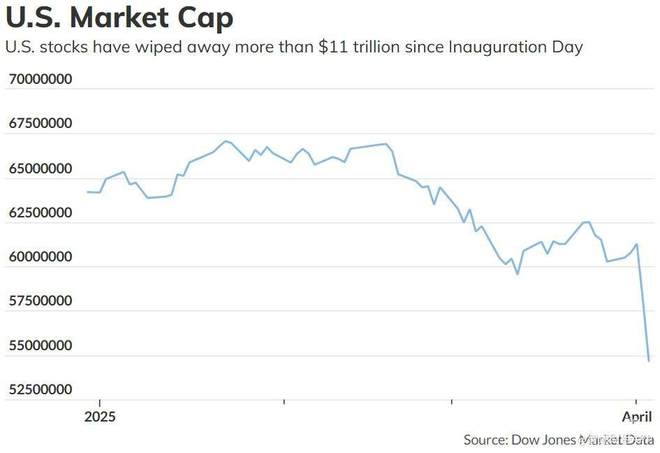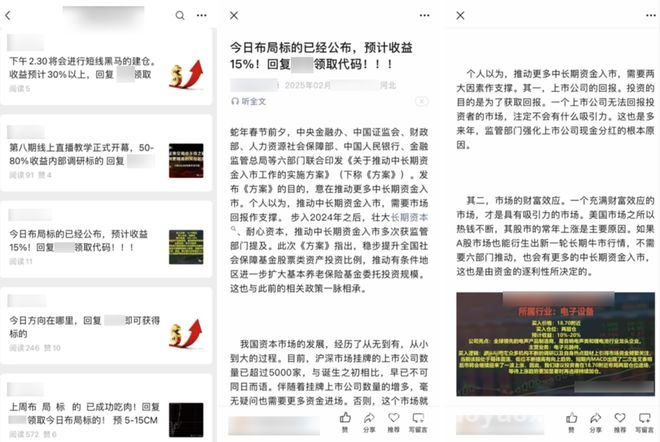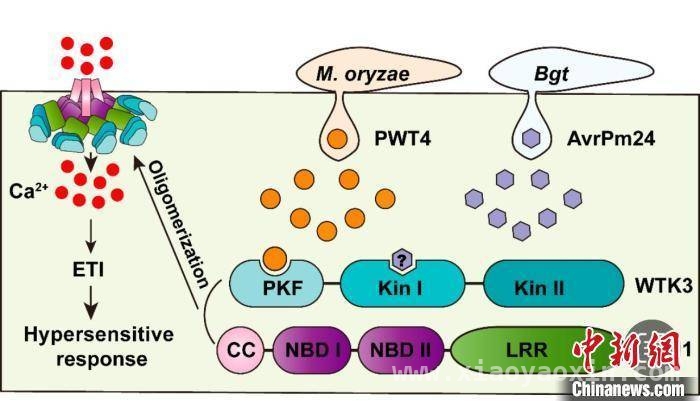诗人木叶的第一本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展开,介绍了诗集萃取了他30年诗歌创作的精华,内容丰富多元。同时还探讨了诗歌的可解与不可解、自由与仪式感等问题,穿插了作者与“闪电花”的回忆,以及对李白诗歌和人生的独特解读,展现了诗歌与生活、历史的紧密联系。


诗人、青年评论家木叶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这本诗集意义非凡,它是木叶30年诗歌创作的一次精心萃取与全面展示。在其中,我们既能看到他对古典与原典的致敬和全新发现,感受到传统文化在现代诗行中的流淌;又能领略到带着先锋精神的新思与新的律动,体会到诗歌突破传统的创新魅力。诗集中的体裁丰富多样,有短小精悍、仅3至5行的当代绝句,犹如灵动的精灵,简洁却意味深长;也有百余行的小长诗和几百行的组诗,仿佛是一部部宏大的史诗,承载着更多的思考与情感。而且,这些诗歌触及的主题广泛,不仅包括诗学本体、语言困境等专业领域的探讨,还涵盖了对人生人性、意义与无意义的深刻省思。
在较长篇幅的作品里,木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他挑战着更多的意义或无意义、纯诗或非诗的界限,同时深入探讨诗歌的自由与仪式感的问题。他在创作中既有对传统的突破,又有对新规则的建立。随着创作历程的推进,他越发意识到关注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就如同关注“人类命运的形式”一般。正如威廉斯所说,“需要在形式上抵达某种深度”。在诗集的后记中,木叶写道:“好的诗歌总是自此时此地此身、自千端万绪缓慢或迅疾地涌起,同时又构成一种超越,一种僭越,迎向无尽的他者、无数的眼睛。”我们仿佛能透过这双眼睛,去探寻他所寻找到的世界瞬间的“闪电和闪电花”。

《闪电花,或总要有个梦永无法实现》(节选)中提到,爱因斯坦说:“宇宙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语充满了诗意,也可视为对诗之为诗简明而神奇的洞见。关于诗歌的可解与不可解、不易解不必解的问题,艾略特所言“真正的诗歌,未待你理解,便会传达真义”也颇值得玩味。这两句话,代表了作者目前对诗歌的综合认知与复杂情感。好的诗歌,就如同神秘的宇宙,展示着所有绽放的过程,它承受着误解,却又赤裸于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之中。
在艰难、危险抑或幸运的时刻,诗人与世界之间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互动,更有可能相互看见,甚至相互发明。就像里尔克所说的“严重的时刻”,这或许是充满挑战的严重时刻,也可能是充满魅惑的奇妙时刻。
诗歌具有独特的属性。一方面,它是自在的,隐秘而偶然,好的诗歌仿佛是一种“无”,它能够逸出作者乃至时代的局限。另一方面,现当代以来,诗歌作为一种存在、一种能量,仿佛在思考着人类,感受着世界。它用幻想校正幻想,用真实锻造真实。有一类诗人主动或被动地为喧哗的时代和骚动的语言“调音”,开始自己的言说,或放声歌唱,不断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自然、新的世界。


电影《帕特森》剧照
《乘一根刺穿越大海》虽是木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但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意外。在这里,他要感谢李宏伟兄的慷慨邀约与默默督促,也难忘在义乌的那个长夜,当时他、黄德海和李宏伟三人在等待一位师友时,各自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近几个月来,木叶一直在做最后的选择和梳理工作,期间打扰了几位可信赖的朋友,未来有机会他会单独写写其中有意味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腾兄,他不仅多年来见证了木叶一些诗的流转,对于诗的取舍和集子的编排也颇有见地。最初,木叶想强调一下“上海诗章”,后来觉得将这一系列作品解散穿插于其他诗歌中更为合适。而且,几乎从有意识地创作新诗开始,木叶就钟情于绝句的形式,多年来他创作了一百余首这样的“当代绝句”,其中三十余首收录在了这本集子里。这些绝句就像一块块会飞的石头,又仿佛悄悄返回枝头的苹果,灵动而富有韵味。
在较长篇幅的作品创作中,木叶持续挑战着意义与无意义、纯诗与非诗的边界,同时深入探讨诗歌的自由与仪式感的问题。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有破有立。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他越发意识到关注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就像关注“人类命运的形式”一样,并且要在形式上抵达某种深度。此外,布洛克的话“诗歌最难传达的意义往往是通过整首诗的音乐和音调揭示出来的”也给了他启示。在诗歌中,一些人与物分裂了“我”的主权,一些字与词托身于万物,一些伤疤与俗常变成了翅羽,一些笑声与沉默化作了刺。美在变得可疑的同时变得强悍而缭绕,恶与罪则不是不可以被蔑视、被打败、被改变。作为作者,木叶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失落与振奋,他提醒自己要淡然、要敞开,然后心怀祈愿。

电影《诗》剧照
当木叶将这些诗整理得越来越清晰时,一个遥远的场景也渐渐在他的记忆中明亮起来。小学乃至中学时,他的多个暑假是在燕山脚下大姨家度过的。有一次到山里游玩,他们来到一处比较偏僻且险峻的地方,途中发现一种花开在石头与树丛之间,这种花艳丽醒目而又略显羞涩。木叶十分好奇,表哥和表姐告诉他这是“闪电花”,还说它在雨中会更迷人。开学后的作文课上,木叶就写了与这种花的相遇。然而,平时喜欢他文字的老师,对这一篇作文却没说什么,只是在“闪电花”旁打了个问号,仿佛在质疑真有这种花,它的学名叫什么。那一刻,木叶失落而又无语。此后,他再也没深入到那片山,也未再遇见这种花,甚至一度忘记它,怀疑它的存在。但表哥和表姐当初肯定的神情,却如在眼前。写此文时,木叶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微信问起了表哥,表哥还记得这种花,不过他说如今山里不少地方没法去,很难看到这种花了,至于花的名字是老人们传下来的,具体没有考察过。
如今想来,很可能语文老师是对的。在生活中,总有些事物近在眼前,我们却未必能识其真容;总有些存在就像无理数π,我们或许懂得如何计算,但却无法将其真切地把握在掌心;总有些发现或爱恨,我们无从准确而传神地表达。于是,木叶也像传说中的古罗马人那样,把闪电和闪电花一同埋入地下,埋入记忆深处。
人的痛苦在于被囚禁于现在,囚禁于此时此地,囚禁于此身之中,但这也恰恰是财富之所在。好的诗歌总是自此时此地此身、自千端万绪缓慢或迅疾地涌起,同时又构成一种超越,一种僭越,迎向无尽的他者、无数的眼睛。
接下来,木叶对李白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他写道:关于唐,他可能比一般人知道的多一些,因此也多出一些悲哀与恨。那一年,战争选择了盛世,也选择了李白和衰老。传说中的昌隆轻轻一触就趋于崩溃,这个民族甚至世界都在此发生巨大的弯曲。李白意识到了什么,从峰峦走出,走向一个人,发出“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言。然而,悲剧也选择了他,浪漫和现实一同卷入“主义”的过山车,他经历了征战、下狱、流放、赦返等种种磨难。于是,正史野史忙个不停,“失节于永王”像“固穷相”一样混入他的人生,既败坏了他的名声,也奇异地拓展了他的形象。
李白看到的自己并不完整,注定会有人不断将不利于他的事和不属于他的诗记在他名下,但他用笑声令历史变得诡谲而可信。虽然没有一首诗能改变一个乱世,但可以改变诗人。高适、岑参甚或王维均有所思有所为,但未能重新发明一种诗学,唯有杜甫做到了。李白喜欢杜甫这个有棱角的人,但似乎还谈不上爱,或许,他和时代一样并不真的理解杜甫。幸运的是,李白和安史之乱一起先是震撼了杜甫、让他的才华得以升腾,后又重重拉回地面,改变了他的视角和语法,诗的维度与难度,进而改变了整个汉语诗歌。
李白既想做侠者,也想做仙者、隐者。他说“不屈己,不干人”,但现实中却满脑子功名,又呈现出一派自然的姿态。他让权力者看到了天才的光芒,也看到了天才的脆弱。他伸手可摘星辰,却不能高声语。他的局限在于从不绝望,也无杀死自己的决心。花儿、美酒与野蛮都生长在他身上,他狂放不羁,与空对饮,与影同眠,他嘲笑孔丘,歌唱苦寒,梦中与童子一起扫落英。所有的诋毁和赞美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像伤口一样的缝隙。
李白年轻时,诗歌也年轻。“噫吁嚱,君不见”是他,“愁杀,妒杀,笑杀,醉杀”是他,“轻王侯,轻九鼎,轻舟已过万重山”也是他。他很多诗是唱出来的,歌且谣,有些东西变成针。木叶觉得自己和李白没有代沟,就像李白和庄子、和敬亭山没有代沟一样。夜深人静时,木叶不免会想,在宣纸上写下狂草“李白”会发生什么?万言不值一杯水,词语依旧,依旧在上升,在上升中坠落。
通过李白,人们懂得了诗歌对诗歌的解放,也体验到了诗歌对诗歌的限制。有人说,如果李白活在今天,依旧意味着自由精神,会弹着琵琶唱摇滚;也有人说,依旧会困于该死的体制;还有人说,依旧会在虚名与虚空中浪游。李白说不清故乡在哪里,也不确定父亲之名,却于举头与低头间为乡愁定了音,并于悲愤与豪迈间命名了万古愁。最神秘的是,他把宇宙视为流动的房间,光是一把钥匙,万物和人在房间中交换身份。在无尽的变幻中,他不断看到另一道光,另一个自己。
李白自身就是一个盛世,由一个个微型乱世构成,或相反;他是一种真,由复杂与矛盾构成;他是一两银子,借助欲念和劳作擦洗自己;他是一只杯子,一次次将破碎斟入完满,或相反。多少个月亮也造不出一个李白,他将月亮抛出去,又将自己抛出去。他谪于天,谪于地,谪于自我。大唐是他的身体,才华都给横溢掉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符号,超级具体而又抽象。在历史的分水岭,他未能重新发明自己,却同时发明了自己的敌人和继承者,他们模仿他,背叛他,重写他,重写世界。就像一度失去杜甫,并注定会反复失去他一样,这个世界拥有李白,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新拥有他。(2024.5)
《乘一根刺穿越大海》中写道:大海是一只灯笼,用火焰清洗自己。你在散步,像一束慢动作的光。一艘巨轮在你的背上滑过,那是天空的一粒棋子。一架飞机坠落于眼前,你绕着它走了一圈。一根无比匀称的刺在你体内生长,弯曲,折叠。你乘着这根刺穿越大海。从出生到死亡,一根刺在你体内;从死亡到出生,一种锋利在你体内。那也是一种完美。你疼或不疼,痛或不痛,你让刺成为自己。你把大海还给大海,你用自身的血与阳光交换。你跃出水面,以内在的锋利领受万有的引力。(2016.5)
本文围绕木叶的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展开,不仅展现了诗集丰富的内容和多元的创作风格,还探讨了诗歌的诸多特性和意义。通过作者与“闪电花”的回忆以及对李白的独特解读,进一步深化了诗歌与生活、历史的联系。让我们看到诗歌既能反映当下的情感与思考,又能跨越时空,与历史和宇宙产生共鸣,带给我们无尽的启示和感悟。
原创文章,作者:小耀,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oyaoxin.com/archives/2462.html